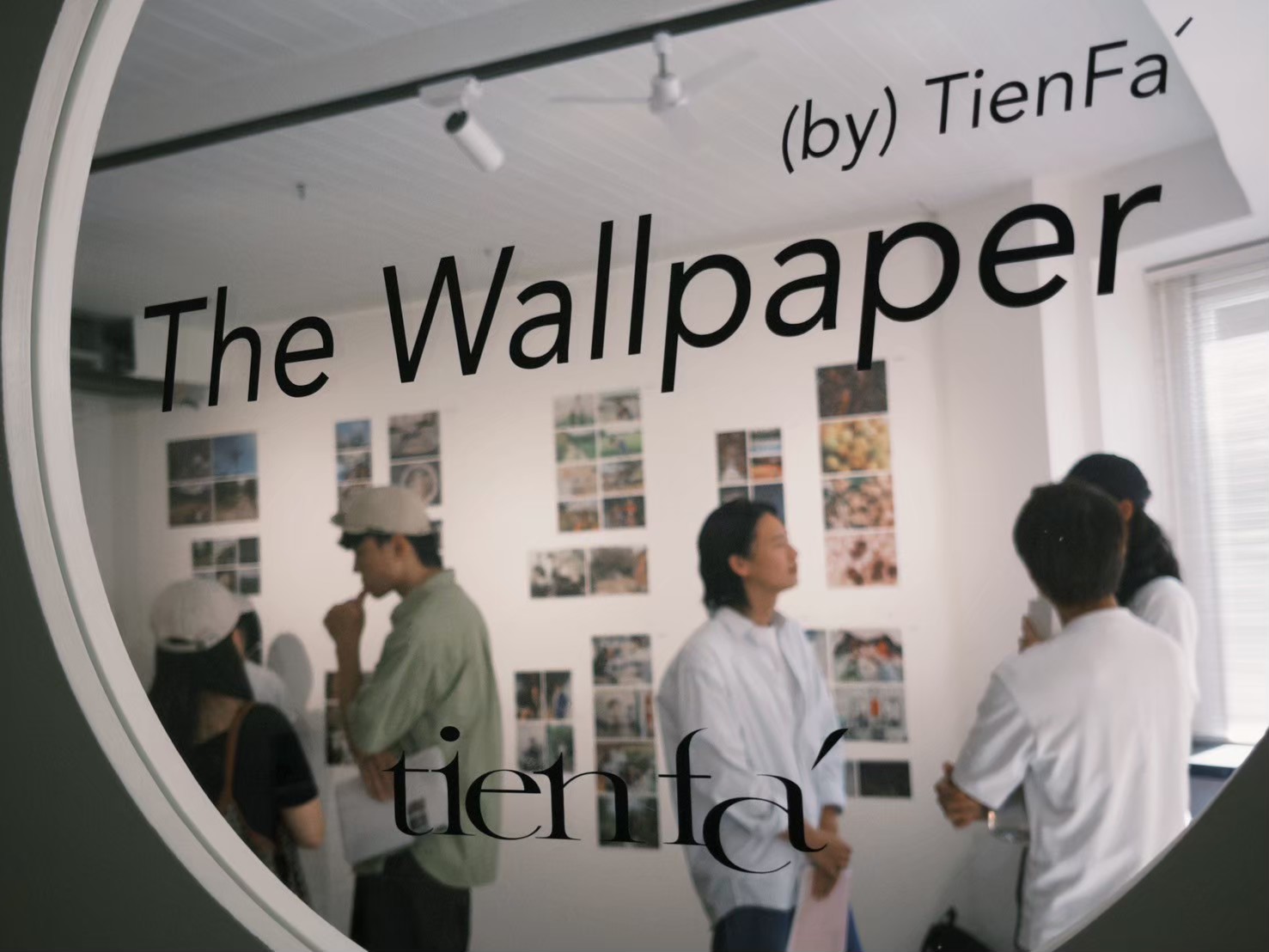gamˊ ngien moˇ ziin moˇ ginˊ ,moˇ oi mˇ cii ienˇ ngiabˋ iangˋ siiˊ vongˊ ziin xiongˇ
文|温伯學
攝影|張天駿 Liszt Chang
圖片提供|汪正翔
汪正翔不只一次提到母親如何影響他走上攝影與藝術創作這條路。
他隱約記得,兒時他曾為了應付學校作業而寫過一首詩,內容大抵是高談「時代的巨輪」云云。母親讀後,只是皺了皺眉頭、不予置評。他感覺到母親並不喜歡,於是又掏出課堂上隨手寫的打油詩:「人家放鳥/你想抓鳥/一抓一放/可憐了鳥」,他忘了靈感從何而來,只知道母親說:「這首比較好。」
說來有些無厘頭的故事,深深牽動了汪正翔的價值觀與面對創作的態度,「我會想,為什麼她會覺得這樣不正經的東西比較好?是因為這樣自然。」

同理,是比對方更早擔憂
回想起母親在身上留下的印記,汪正翔說,那是一種很隱微的影響。
記憶中,相較於外省背景的父系家族,總要求孩子必須背誦唐詩、強調「詩書傳家」;留著客家血液的母親,只在日常中帶著他和哥哥一起看電影、讀小說。「我媽為我做任何事,從來不會掛在嘴巴上,並不是因為她忍耐,是根本就沒有那個習慣。」
一切行為都是不溢於言表的,把善意藏起來,這是汪正翔認知中最「客家」的一件事。
同樣的態度也體現在他擁有的頂級放大鏡和相機上。汪正翔和哥哥皆患有先天的眼疾,因此母親置辦任何關於視覺的用品總是不手軟,比添購吃穿更加用心,是彌補、更是寵溺,要他們在真正失去之前盡情揮霍。然而這些苦心她從未說出口,只是給予。
「這個事情讓我心態很微妙,眼睛越來越不好當然有點哀傷,可是同一時間你也感覺到,有一個人在你之前擔憂這件事。有時候同理或是關懷,不是表現在付出善意,也不是表現在給我的這些東西上,而是她比你更早去憂慮這些,甚至比你還憂慮這些。」
旁觀的「客家攝影師」
我們和汪正翔散步在廈門街,踏查曾經的外婆家。他在一顆老楊桃樹下駐足,向上指了指,「我就是在這裡度過了整個童年。」他和外婆、母親的關係親暱,但卻始終只會說那麼一句客語——還是為了想和超級賽亞人一樣酷才特地學的——亻厓係盡強的人(我是很強的人)。
汪正翔的外婆來自苗栗公館,外公事業有成後,才舉家搬遷至古亭一帶。「那個情況,就像去到紐約的移民,必須努力融入新環境。」汪正翔事後猜想,或許成功的移民,必然得要隱去自身族群的特色才能立足,那些從客庄帶來的語言和文化,久而久之就成了大都會裡的白噪音。
汪正翔沒能繼承母親的語言,開始創作之後,也始終和「客家文化」保持著旁觀的、曖昧的關係。
有段時間,他常在社群上半開玩笑地自稱是「客家攝影師」,甚至一度想以「反客為主」為題申請展覽,他解釋:「客家相關的展覽,總是請別人去拍客家人,這沒有客家的主體性啊!應該要找客家人去拍別人,才有主體性。」
以當代創作的角度挑釁一再強調身份認同的社會。這樣的發想完全反映了汪正翔的創作理念:不在意表面的漂亮,而是盡量真實地去戳破表象,做出令人發噱且值得省思的作品。


混進光的影子,或混進影子的光
訪談當日,正處乍暖還寒的二月天,汪正翔剛從里斯本駐村回台。「歐洲的一切對我來講都太耀眼了。」他形容,歐洲與臺灣就像光與影的關係,身為臺灣的藝術家,他希望能做出關於家鄉的作品,但又不想一切太過順理成章,於是決定在里斯本的攝影棚裡佈置出臺灣風格的「歐式婚紗沙龍」。
「我真正想做的,不是把臺灣帶到世界,而是把這些我也不是很確定的荒謬元素跟西方文化結合在一起。這樣你就很難說什麼叫做最正宗,什麼又是衍生的,因為一切都混在一起。」一邊把影子帶到光裡,一邊挖苦著歐洲霸權、也挖苦自己。這樣有些「不正經」卻出於真實感悟的創作精神,與他幼年時寫下的那首打油詩如出一徹。
這些年來,汪正翔持續遊走在攝影、藝評、策展、教學等領域之間,不穩定的身分讓他時刻焦慮,牢騷一路從Facebook蔓延到Threads。
問起近日的煩憂,他向我說道:「雖然偶而還是會想『我是否成了一個專業的藝術家』這類的問題,但我也會想到我媽的態度,她比較在意的,還是你是否對這些事有自然的喜好。這會帶給我一些安慰,就好像有個隱微的聲音在跟你說:就做你喜歡的,而且這件事是值得被肯定的。」
一件與客家羈絆的物件:放大鏡
手上的放大鏡不是當初母親送他的那一副,但卻是母親死後汪正翔費盡心力才找到的同一個品牌的產品。終於找到時,他才知道母親為他買的是一款德國製造的頂級放大鏡,不是隨便買的,恰如兒時哥哥有次把母親送的數位相機弄丟了,母親隔天立刻再買了一臺——這一切,她從未多說,很多事情兄弟倆後來才知道。